鱼生于自然,唐小说中的鱼以及鱼文化,你了解多少?
鱼,作为水产鳞介中的一员,历来是人类食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公社时期,中国古人就开始结成渔网捕捞鱼虾等水产。伴随着古人对鱼类这一生产对象日益频繁的捕捞、饮食、养殖活动,人们对于鱼类的认识越发深入,并将鱼的种种特性迁移到精神层面,演化出丰富多彩的鱼文化和鱼故事。

唐代是中国鱼文化的高峰期,生发种种鱼故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唐小说中载有大量涉鱼故事,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梳理相关内容,研究唐小说中的鱼类书写内容和书写方式,对于了解唐代社会各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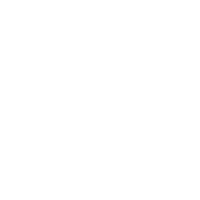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一、唐代渔业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也是鱼文化的中兴期。唐小说站在现实与想象的交汇点,其中的涉鱼笔墨亦根植于现实,向虚拟和梦幻处衍生。唐代渔业经济极为发达。
养鱼捕鱼是渔业经济活动的基础。我国最早的养鱼著作《陶朱公养鱼经》虽早已亡佚,但于《齐民要术》中仍有部分遗存。陶朱公范蠡认为经营货殖、发家致富有五种方法,养鱼为其中首选,说道:“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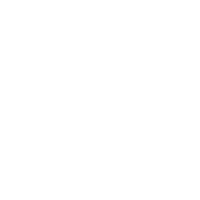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所谓水畜者,鱼也。”。只要在六亩大小的水池中放入二十头怀子鲤鱼和四头牡鲤鱼,池中置鳖,就能轻易得到无数鲤鱼,年年获利不尽。文中,陶朱公将鱼鳖混养的好处归结于鳖为神守,可以防止群鱼随蛟龙飞去,充满了奇异的想象。
这种说法于今天而言也许不够科学,但其做法立足于过往养鱼经验,确实行之有效、立竿见影,故而陶朱公养鱼法历代均有承袭应用,李白《襄阳曲》其四即为歌咏依陶朱公养鱼法而建的习家池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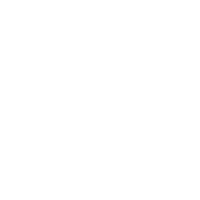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与此相对应,渔民作为一种身份和职业在唐代极为普及,唐小说中多有提及。以《太平广记》为例,《高昱》中隐士高昱以钓鱼为业;《陈君棱》中主角自小捕鱼为业等等。
养鱼之外,唐代捕鱼工具也品类众多、种类齐全,皮陆二人的诗文集记载颇全。陆龟蒙在十五首《渔具诗》列举了十五种渔具及相应渔法,仅网就有罛、罾、罺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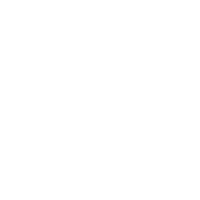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皮日休在唱和的《添渔具诗》又补充了鱼菴、钓矶、蓑衣、箬笠、背篷等五件渔业相关用具,认为两人诗文已将渔具和相关技巧罗列齐全、一网打尽。除了渔具,水獭、鸬鹚等动物捕鱼方式也在唐代多有应用,全唐诗和唐小说中均有多处记载。
观鱼活动在养鱼捕鱼的基础上产生,是唐代统治者和上层贵族的常见休闲方式。《唐书》中记载了太宗在西宫观鱼之事。唐时渔夫用饵食来吸引游鱼,引得鱼群跳跃不止,最后一网打尽,太宗在旁观察,不时发问,显然乐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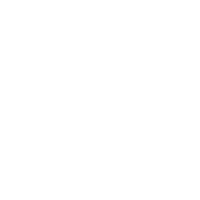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以上种种,展现出养鱼捕鱼技术在唐代已相当成熟完备,观鱼记鱼等衍生活动也深受唐人喜爱,为鱼文化和鱼故事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唐代饮食中的鱼文化
唐人享受世俗生活,侈于美食。唐代宫廷菜水陆鲜珍应有尽有,水产尤受偏好,口味上则偏向清淡中和,不借助胡椒、肉桂等调料,却能极尽美味。在各式菜肴中,加工程序较少的鱼鲙倍受青睐,在唐小说中出现的极为频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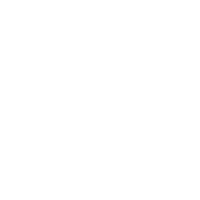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明皇杂录》曾记房琯被邢和璞卜算将因鱼鲙死亡,多年后路过阆州紫极宫预言果然应验的故事。鱼鲙虽然美味,但在死亡前往往滋味尽失。一般人畏惧死亡,逃避死亡,听到类似的预言必定对鱼鲙畏之如虎,从此罢箸。
房琯却能毫无为难之色,明知生命即将终结也要欣然赴约,食尽而归,其性情之坚毅,精神之豁达实在令人拜服不已。唐人宴席也和鱼类密不可分。烧尾宴作为庆贺宴席,一般用于两种场合:一是唐时大臣宴请皇帝庆贺升迁;二是新科士子庆贺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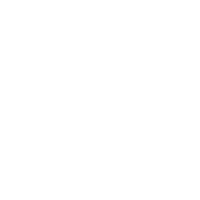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其取意有三种,分别是鱼、虎和羊这三种动物烧尾后变成另一种生物,寓意身份、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贞观年间,唐太宗问朱子奢烧尾之事,后者便用羊烧尾解答,然而唐人及后世诗文提及烧尾多专指鲤鱼化龙之事。
“鱼将化龙,雷为烧尾。”“烧尾”作为鱼化龙的尾声,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意味着脱胎换骨和青云直上。虎烧尾仅是变为人形,羊烧尾仅为融入新环境,吉祥进取的寓意均稍显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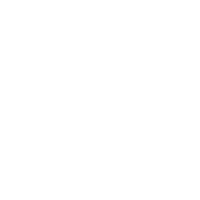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除此之外,唐代还有佩戴鱼符的说法。鱼袋的用途为盛放鱼符,为五品以上官员专有,其饰色与官员的品级服色相挂钩,凡三品以上穿紫服者赐金鱼袋,五品以上穿绯服者赐银鱼袋,故称赐金紫、赐银绯。
武后当政时期曾将鱼符改为龟,鱼袋改为金银铜三等,中宗当政后又恢复了旧制。符瑞袍服的变化与时局形势紧密相连,然而即使是天下无事的太平时期,官员们的仕途前程与吉凶祸福也难以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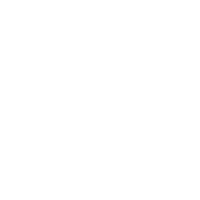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唐小说中常常有借袍服变化代指官运休咎的情节。《戎幕闲谈·范氏尼》中颜真卿认为能够官居五品,穿绯衣,带银鱼,子孙候补斋郎这样的小官便可心满意足,为他卜算吉凶善恶的尼姑范氏则借紫丝布食单暗示颜真卿未来官阶之高。
仕途前景是是预言者反复强调的部分,也是人物生平的重要节点和除生死外最为关心的部分。这则故事借僧侣道徒、奇人异士之口先行说出人物命运,再让含混不清的预言一一应验来展示天命的权威和不可违逆,展现了文人仕子对前途命运的不安,天命只是他们寻求稳定和安慰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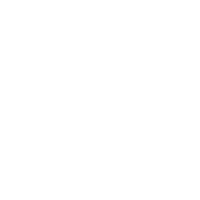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三、鱼与民间信仰
唐代信仰环境宽松,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本章以唐小说为主要材料,从民间信仰、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三个方面分析鱼在唐代宗教信仰中的角色。其中,鱼在民间信仰中从祭祀对象转为神灵侍从,展现了理性观念的上升。
唐代民间信仰昌盛,除却天地山川、祖宗之灵等传统祭祀对象,自然现象、动植物、人使用的物品等都可以进入信仰的世界,供人祭拜,每一乡里不但必有庙舍,而且经常不止一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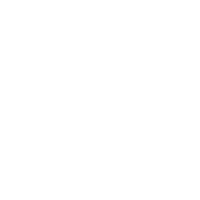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这些民间祀庙四处收罗信徒、妄言福祸凶吉,积弊甚众。鱼作为民俗祭祀的一部分,除了祭品,通常以祭祀对象、神灵侍从两种身份出现在唐小说中。鱼被奉上祭坛成为祭祀对象,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动植物崇拜。虽然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一以贯之、变动不大。
魏晋小说中《鲍君》《鮔父庙》等记淫祀来历的篇章已能让观者感到众多民间神灵的兴起经不起认真考量,但唐人仍续其遗风,好兴淫祀,各种鱼类也能成为神灵,享受祭祀。
鱼为水虫,神职多与水有关,然而鲍君、鮔鱼、无支祁、掘尾、逆鳞鱼等动物水神毕竟形象鄙俗怪诞,难登大雅之堂,故而大多只能局限偏壤之地,为一乡一里之民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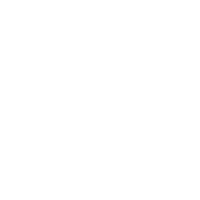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于是水族外众多人类形象的“外来户”得以顶替鱼类等动物水神地位成为水神主体,两者一道合成了水神整体。水神们诗歌主题看似分散,实则统一,可以当做社会各阶层人士面对唐后期统治失御、积弊甚深的危急局面时的焦灼痛苦和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是一个问题不同角度的投射。
结尾水神们借聚会掀起狂风大浪,发出“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的呼声正是唐末百姓饱受欺凌后揭竿而起掀翻一切的预言。在底层百姓眼中,不管祭祀的神灵是人是鱼、姓何名谁、甚至是否真实存在都不重要,只要能够祈求福祉、抚慰心灵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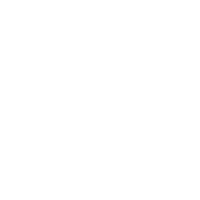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在统治阶层眼中,民间祭祀既耗费人力物力又触犯自身权威,打击淫祀应当不遗余力、毫不留情。百姓的愿望让虚构的神灵拥有力量,也让解释者拥有话语权和权威性,进而产生同上层统治者博弈的力量,故而“淫祀”存在与毁灭的原因是同一的,民间土壤不灭,神灵就不会消失。
四、总结
唐人作意好奇,唐小说中存在大量摹写天地自然、奇闻异物的篇目,常被归入志怪 述异一笔带过,鱼仅为其中一种,却又对于唐代有着特殊意义,值得被人认真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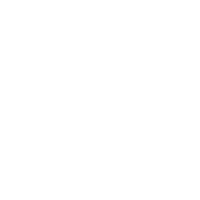
唐小说中涉及鱼书写的篇目数量众多,不仅记录了唐人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也折射了他们对宇宙万物和个体生命的体认与思考。首先,唐代是鱼文化的高峰期,鱼以食材、符瑞、饰物、墓葬用品等形式出现在唐人生活各个角落,亦在小说中展现了唐代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和丰富多样的人物性格。
唐小说中的鱼书写展现了唐人的昂扬向上的文化品格和细腻丰富情感世界。自然之鱼涵盖大量地理博物志怪内容,反映了唐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认识
声明:本站属公益性没有商业目的的网站,上列文章仅供个人学习参考。本站所发布文章为原创的均标注作者或来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许可转载的请注明出处。本站所载文章除原创外均来源于网络,如有未注明出处或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
欢迎关注本站(可搜索)"养鱼E线"微信公众帐号和微信视频号"养鱼一线"以及头条号"水花鱼@渔人刘文俊"!

